-
日期: 2023-09-06 | 來源: 知識分子 | 有0人參與評論 | 字體: 小 中 大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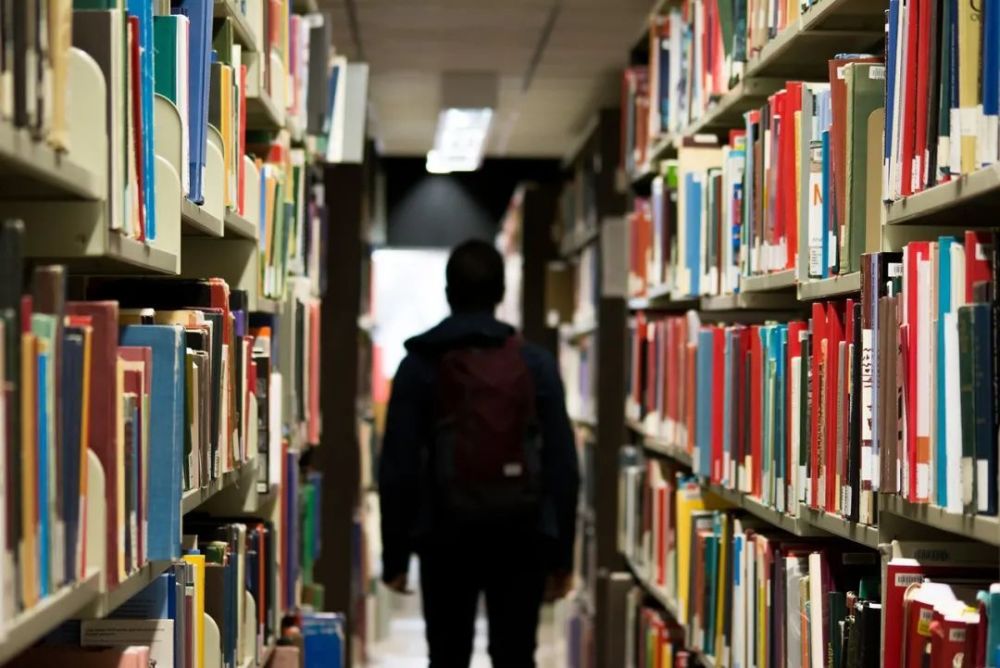
當地時間8月28日,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,34歲的博士研究生齊太磊涉嫌在實驗室開槍打死其華裔導師嚴資傑。29日,齊太磊被控犯有一級謀殺罪和校內持有槍支罪,並首次出庭,法官將聽證會時間定於9月18日。
《時代聯盟報》引用嚴資傑的導師 Doug Chrisey 的敘述,Doug Chrisey 稱,在今年7月,嚴資傑向他提及自己的一位學生有精神健康問題,“他希望這位學生能夠盡快畢業,也向相關部門報告了這一情況。”
“研究生院的科學研究很艱苦,由於常面臨實驗失敗和論文被拒,學生們的壓力非常大,”Chrisey 總結。
數據顯示,21世紀以來,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增長迅猛,從2000年的3.9萬到2019年的70.35萬。1978年至2019年,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.06萬。
2013年,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刊發了一項研究,研究者對耶魯大學130位中國留學生進行調查,發現45%的人報告有抑郁症狀,29%的人報告有焦慮症狀。然而,在受訪者中,27%的人從未聽說過學校的心理健康咨詢服務,只有4%的人用過這項服務,但後者也多為漫長的等待、有限的咨詢時間所困擾。
2022年,在Covid-19流行期間,一項面對中國留學生的研究顯示,由於社交隔離、線上教學等原因,64.9%的人群感到焦慮,其中22歲以下留學生的焦慮患病率(68%)高於22歲以上的群體(61%)。
北卡校園槍擊案本身目前還需更多的信息,但該事件延伸出來的另一主題值得關注:當代留學生的現實處境和精神心理狀態是怎樣的?他們需要怎樣的支持?
我們為此拜訪了廖元辛。他在北大畢業之後,赴美國馬裡蘭大學攻讀公共政策專業碩士。2015年畢業後,他走訪美國19個州,30多所高校,訪問了100多位中國留學生,並於2018年出版了《新留學青年》一書,講述了這一代留美學生的真實生活。
“留學生在海外,明顯脫離了親情磁力場,沒有父母的注視,遠離親戚,人際關系也無法與國內相比,”他試圖總結,“好像身處曠野之中。”
他引用了一位紐約心理咨詢師的敘述,“定義自我、尋找自我認同的過程,是每個年輕人都要經歷的。但對於留學生來說,連續的自我認知發展過程因為留學而突然被切斷,再到一個學業、生活、社交各方面都處於高壓狀態的環境中重塑,就會造成很多挑戰。”
以下是他的敘述:
身處曠野
留學生出國之後,首先面臨的是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沖擊。
比如“城與鄉”的巨大差異。在美國,很多學校建在鄉下,雖然叫“大學城”,但城鎮都是圍繞大學發展而來的。但國內,許多大學都集中在大城市裡,留學生離開國內熱鬧的城市生活,來到美國鄉下的大學城,就會面臨許多新的挑戰。
關於“鄉居”生活,不單單是指生活不便利 ——以我自己在馬裡蘭的日常為例, 平時坐校車要經過15分鍾山路;唯一的商業區是散落在一塊停車場四周的幾家快餐店和服裝店,去任何便利店都要開車;周末沒有校車,出門理個發,一個上午就過去了。
更重要的是,包括我在內,很多留學生會感受到一種置身“世”外的疏離。在北京、上海、紐約、波士頓這樣的大都市,不管是奧運會、世博會還是時裝周、馬拉松,個體即使無法真切置身其中,也多多少少會有時代的參與感。但對我來說,“熱鬧是它們的,我什麼也沒有”,過去20多年的城市生活被隔斷重新塑造。
很多人也會感到強烈的孤獨感。比如我的一位學姐,在給我的信中,她提到最多的一個詞就是孤獨。她是在印第安納大學讀書,剛抵達布盧明頓時(學校所在的小鎮),每天哭著給母親打電話,連續哭了19天。
因為美國的人際界限相對明確,每個人更關注自己的家庭和生活。留學生背井離鄉,沒有國內溫暖的人情磁力場,遠離家庭、親戚和朋友,也缺少兜底的安全網。
總結自己的留學生活,我會用一個詞來概括,“曠野”。如果說孤獨是一種心境,“曠野”可能就是一種完全依靠自己的狀態。
美國社會更強調魯濱遜精神,社會對個體的期待是,無論工作還是學習,一切都要依靠自己。很多時候,沒有人給你兜底,你必須面對日常的細枝末節。所以很多留學生在海外至少學會兩件事:開車和做飯,即使沒學會開車,也要學會通過導航找到回家的路。
再比如搬家,我們在國內可能都已經習慣了在手機上輕松下單,就有師傅來打包搬運。但在美國,很多時候都需要自己去租搬家用的卡車,甚至要自己駕駛。這些事情,你搞不定,完不成,很難指望別人來幫你。
除了環境之外,留學生普遍面臨的另一個沖擊是,隨著社會對自己的評價標准發生變化,個體會感受到強烈的落差,從而影響心理和生活狀態。尤其對於新入學的留學生來說,這種情況更是普遍。
在國內,“好學生”的評價標准相對單一,那就是學習成績好。比如我的一位訪談對象,初中時參加奧林匹克物理競賽,成績很好,是學校裡的“名人”。高一移民到美國後,他發現當地關心奧林匹克物理競賽的人沒國內那麼多。相比之下,美國的高中生覺得最酷的是,男生打橄欖球,女生做啦啦隊。這種情況下,他的自我認知就會受到沖擊。
我的另一位訪談對象也是如此。這是我的一位師姐,我們住所很近,也經常聊天。她從北大畢業後到美國讀研究生,她在國內的成績和實習履歷都很好,外形也很好,所以一直覺得自己在評價體系中理所當然地應該占據很好的位置,得到更多人的喜歡。但到了美國之後,評價體系更加多元,原本在她看來“來自國內二三流院校的同學”反而在很多方面更受歡迎,為此她深感挫敗。
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?因為在美國,大家不在意你是否來自清華北大,而更注重你對學業和工作是否投入,是否尊重他人,是不是一個好的團隊合作者。
另外,國內外教育體系和人才培養模式的不同也會給留學生帶來挑戰。
比如說,在國內,普遍存在著讀完本科讀碩士,讀完碩士讀博士的思維方式。大家總覺得,碩士優於學士,博士優於碩士。
但在歐美各國,讀博士和讀碩士,是完全不同的發展路徑。博士是以培養學術研究者為目標,是進入學術界和高校教書的敲門磚。
而碩士則是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的敲門磚。比如有人當了五年中學老師之後,如果想從商,就去商學院讀一個master。
因此,在碩士項目中的外國人,大都有工作經驗,他們目標明確,讀什麼,去哪裡讀,讀之後做什麼,都有自己的回答。中國留學生則與之相反。我在修一門名叫公共管理的課程時,任課老師之前在政府部門任職,我能聽懂她說的詞句,但無法想象其描述的工作場景——這對於普遍缺少工作經驗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常事。
這跟國內用人單位青睞學歷高的應聘者不無相關,學歷影響著錄取和起薪,甚至未來的升職調動。同樣一份工作,一個22歲的本科生,和一個24歲的研究生,很多國內用人單位會傾向後者。
因此,很多中國留學生和家長大都把學歷當做跳板,留學生茫然地出去,茫然地畢業。很多人還處於自我探索的過程中,並不清楚專業是否是自己喜歡的,怕犯錯,也更容易犯錯。
那些普通沉默的大多數
我想寫一本關於留學生的書,想法最早起自2012年“南加州大學槍擊事件”,兩名中國研究生在洛杉磯校區一英裡外,在二手車內被槍擊身亡。但媒體報道引入了“二手寶馬”等字眼,一時間,關於當事人“富二代”“官二代”的猜測鋪天蓋地。但事實是,他們二位都出身普通家庭,求學生活也很簡樸。
這種對留學生群體“標簽化”的討論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後來,我讀梁鴻的《出梁莊記》,作者指出,隨著農民工群體被社會不斷符號化、標簽化,人們對農村、農民和傳統的想象越來越狹窄,對幸福、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。
盡管留學生和農民工之間存在千差萬別,但有一點是相同的,社會對他們的標簽化程度不斷加深。
在我寫作的那一年(2016-2017),有35萬名中國學生前往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學習。然而,在媒體的敘事中,他們中的大多數都面目模糊且沉默。當我搜索關於留學美國的信息時,看到的要麼是“哈佛女孩”的勵志故事,或者是開跑車住豪宅,亦或者是其他一些在美國升職加薪的成功學的案例。但大多數留學生是怎樣的生存狀態和心境?他們在學業、社交、生活和家庭等方面都面臨著哪些挑戰?這些都少有人關心。
我感覺,社會對留學的理解,好像還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印象。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,中國出現了“出國熱”。那時,中國留學生主要有這些特點:
大多數人的背景相對統一:公費,學科集中在理工科,拿獎學金攻讀博士。這些留學生中,60%~70%來自北京和上海的高校,這個其實並不難理解,在沒有互聯網的背景下,這兩個城市獲取海外信息,比如學校、學科專業、老師等信息,相對更容易一些。
當時出去的留學生普遍都沒有什麼錢,無論是去歐洲還是美國,很多人下飛機的第一件事,不是去學校報到,而是直奔中餐館刷盤子,以確保生活來源。
一些書和影視作品都曾反映過那個時代背景下留學生的處境,展示他們的心酸,比如大家印象比較深刻的《北京人在紐約》。
那時候,國內和海外的經濟差距比較大,許多人想在畢業後獲得工作簽,比現在容易許多。數據顯示,2000年之前,每年赴美的人不超過兩三萬,但當時美國每年工作簽的配額大概有十幾萬,競爭遠沒有現在那麼激烈。
相比三十年前,當下留學生群體的背景和構成都出現明顯的變化。首先是人數成倍增長,這也意味著競爭壓力增大。尤其是讓一些中國留學生談之色變的H-1B簽注,每年數以十萬計的中國留學生和印度、拉美學生參與抽簽,抽中之後,可以在美國合法工作三年(此後如有需要,可以申請再延長,再次到期則不能延長,只能選擇其他類型簽證或綠卡)。
這些年,國內經濟飛快發展,家庭環境都有了明顯變化,大家都有一定的資金,留學生剛下飛機就去刷盤子的情況也不再是普遍現象。同時,留學專業選擇也多了起來。過去為了獎學金,很多人選擇理工科,但現在,讀藝術、讀電影,各行各業都有。
低齡留學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。在我成書的時候(2016-2017),中國赴美留學生中,低齡留學生、本科、碩士及以上的比例已經達到了1:2:2。
另外,與三十年前相比,還有一個關鍵變量——獨生子女,這一點無論對留學家庭還是留學生本人都有著深刻的影響。在獨生子女政策之前,一個家庭有好幾個孩子的情況下,家庭中對單個孩子的期待不會那麼高,投入也不大,當他們做出未來的人生規劃時,家庭也不會有多大的幹預 —— 如果一個孩子留在國外,父母年齡大了,還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顧。
但獨生子女政策實施之後,這一代留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壟斷了家庭所有的教育資源。他們的父母,其中一些人可能受益於恢復高考之後高等教育的發展,也願意傾盡全部給孩子提供好的學習機會。在這一過程中,許多父母逐漸成為留學生專業、學校選擇的主導者。
我見過許多留學生家長,他們對留學的認知、和孩子的溝通方式都會對孩子產生影響。一些家長基於自己的經歷、知識結構和視野,可能對海外生活非常了解,對於很多事情有自己的判斷,這對他們和孩子的流暢交流奠定了基調。
相比之下,一些家長缺少對海外的了解,在微信群裡人雲亦雲。也有一些家長認為,把孩子送出國就算任務完成,對於孩子後續生活缺少關注的動力。當孩子留學遇到困難時,家長可能會無意識地弱化困難,這會導致孩子傾向於報喜不報憂。因為在孩子看來,如果父母不了解自己所面臨的處境,報憂只會加劇他們的焦慮,不但無益於問題的解決,還會讓自己承擔額外的壓力。
一些留學生願意和我聊,讓我把他們的經歷記錄下來,也是希望以我作為“第三方”出口,讓父母更多了解自己在國外留學的處境。
對於獨生子女來說,父母也在他們未來的人生規劃中占據特殊地位。我看過一份十年前的研究,提到對於在美的中國留學生(主要是獨生子女)而言,影響其未來是否留在美國的幾個因素中,父母是排首位的。那幾年,關於中國空氣質量和PM2.5的討論鋪天蓋地,但研究顯示,就留學生的選擇來說,環境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影響因素。
我的一位訪談對象就提及過自己回國的原因,“我一出國,家裡就剩爸媽兩個,我沒有辦法照顧他們”。他的媽媽年輕時有心臓病,一次輸液差點休克,那時他還在國外讀研,因此一畢業,他就立刻回國找工作了。
抑郁的留學生們,只是講出來都很困難
觸發留學生抑郁的因素很多,前面就有提及來自環境、社交和學業帶來的挑戰。
我想重點提兩個群體。一個是低齡的留學生,他們本身處於探索自我,塑造世界觀、人生觀的階段,如果環境出現劇烈變動,對他們的影響會很大。
另外則是博士群體,因為從PhD的申請開始,一路都充滿了不確定性。學校的錄取委員會雖然會把GRE和托福的分數、推薦信和科研成果的含金量作為重要的參考指標,但最終錄取的結果不像單純的考試成績那樣,掌握在申請人手裡。這是在申請讀博時會遇到的問題。
而在正式開始讀博後,挑戰依然很多。比如我的一位訪談對象,他曾是大家認為的那種“適合做學術的人”,頭腦聰明,能夠沉潛做學問,定力十足。但與許多苦行僧的學霸不同,他也享受生活,是班裡籃球隊的主力大前鋒。
然而,他在美國讀經濟學PhD的時候,嚴進嚴出的標准也讓他感受到巨大的壓力。他告訴我,第一年還只是“知識的純消費者”,看教材、做題、考試。第一學期結束後,會有一次資格考試,通過後才能繼續讀PhD,項目中十七八個人,四五個沒有通過這一考試,只能退出。
其他學校的淘汰規則更為嚴厲,實行按比例淘汰。
讓他感到更吃力的是第二年,他從“知識的消費者”轉變為“知識的生產者”,要嘗試自己建立模型,去解釋現象。
在我完成書稿的幾年後,我們在北京相遇,他在第三年選擇退出,重新讀法學博士。相比自己建立模型,可能理解、闡釋法條對他來說,更容易一些。
在一些理工科專業中,如果是跟工業界聯系更緊密的學科,退出之後就業相對容易;但對於一些基礎學科的學生來說,出口相對更窄,路徑單一,可以說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。
在這樣的處境中,不少人逐漸出現抑郁情緒,但很多人都不自知,仍在苦熬。
我曾有過類似的體驗。2015年,因為工作的迷茫、是否回國的焦慮,以及感情受挫,我曾陷入半年的抑郁情緒。天亮才能入睡,午後起床,醒著的時候要麼打游戲,要麼等待天黑,繼續入睡。
朋友找我打球或外出游玩,我也躲著他們。甚至連吃飯、洗澡都變得極為困難。當年8月,我回國見到父親,他說,“你該多運動”,但事實上,這並不由我主觀意志主導,面對我的狀態,他變得焦慮,則更讓我寢食難安。
我在做訪談時,發現許多留學生都有類似的處境,但大家彼此從不或很少交流,總覺得自己是“異類”,是旁人無法理解的。當聽我說,“我也經歷過”“我采訪的留學生中,抑郁情況相當普遍”時,他們的眼睛突然亮了。我那時候逐漸認識到,講述抑郁是如此艱難的一件事,我們也缺少窗口,看到他人也如自己一般困頓其中。
事實上,美國本土學生的抑郁率其實也很高。在2021年-2022年裡,研究者對美國 133 所高校中 96000 名美國學生進行調查,其中44%的學生報告有抑郁症狀,37%的學生報告有焦慮,15%的學生在過去一年考慮過自殺——這是過去15年來調查歷史上最高的比例。
中國留學生面臨的處境、觸發抑郁的因素和當地人有很大的差異,很多時候很難有參考價值。如果一些高校沒有面向留學生的心理支持體系,語言障礙、文化差異可能確實會讓人在尋求幫助時卻步。
我向一位訪談對象詢問,“如果有機會,會向未來計劃留學的學弟學妹建議什麼?”她告訴我,學校的心理咨詢依然是最佳的求助選擇,有的學校配有講中文的咨詢師。
“效果未必立竿見影,但他們至少可以幫你找到解決問題的出路。以後如果再出現類似的情緒,你就會不慌了。就像感冒,第一次感冒治好了,以後再發燒咳嗽,你就知道要怎麼面對了。”-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,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!
- 佛州大學槍擊案嫌犯:極端觀點與混亂童年塑造人生
- 假山假景假臉,央視《藏海傳》爆火,打臉內娛多少"垃圾"古裝劇
- 本周加拿大最低的房貸按揭利率
-
- 慘烈車禍三名青少年喪生 是他們!
- 大佬組團收購 溫村MEC回到加拿大
- 溫哥華牙醫 采用先進技術最新設備
- 笑懵 視頻瘋傳大溫黑熊推賽博皮卡
- 宋慶齡養女去世 病因曝光 生前煙不離手
- 川普大赦免 只要有錢 找對牽線人 立場正確
-
- 溫哥華地產經紀 經驗豐富誠信可靠
- 懵 溫村這裡居民想續租交百萬稅款
- 加國移的民!78歲老頭涉嫌性侵幼女
- 卡尼"跪"了:對美關稅近"清零" 全網怒轟
- 智庫:加國聯邦應裁員6.4萬 省百億
- 美越貿易談判之際 越南豪送川普集團15億美元
-
- 美公開現場照 何立峰小心翼翼"落後半個身位"
- "休戰"90天 中國對美出口商樂觀不起來
- 習實錘喪軍權!?吳謙退場 三新軍校"去習"
- 中國工廠"電話被打爆" 美國客戶急瘋了
- 當街槍殺兩人!加拿大全國通緝兩青少年
- 新冠再來襲,專家提醒:當前正處於小波峰
-
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,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